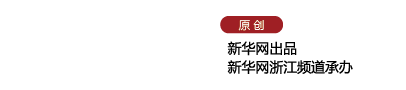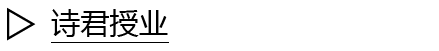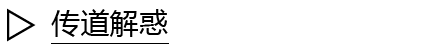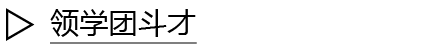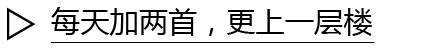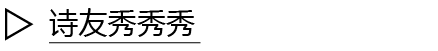这首如今连小学生都会背诵的唐诗,开头两个字却在明代引起了一段公案。明代大文人杨慎在《升庵诗话》中说:“千里莺啼”,谁人听得?千里“绿映红”,谁人见得?若作“十里”,则莺啼绿红之景,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皆在其中矣。杨升庵之后论诗者多有辩驳,此处不再赘述。
我想说的是,虽然千里已成定谳,但杨升庵的话也自有他一二分道理。升庵精通画理,而诗理与画理相通。杨慎的十里,指的是一幅山水小景,尺幅之中,村郭酒旗皆在,小中见大地绘出江南春色。
但杜牧的野心不在于此,他要说的是更为宏大范围的故事,第三句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,笔力一转,再现了南朝,尤其是梁武帝时期举国佞佛的场景。梁武帝在南朝皇帝中文治武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,晚年北朝大乱,东西魏分裂,干戈不绝,本来是统一中原的绝好时机,但他却沉迷在佛教中不能自拔,昏招频出,不但坐失大好时机,还几乎给南梁带来灭顶之灾。只今唯剩烟雨楼台,述说当时的遗恨。
本诗作于唐宪宗晚年,宪宗早年时任用裴度、李愬平定叛藩吴元济,诸藩震慑,号称元和中兴,晚年沉迷佛教,诸藩再度不臣,大好形势拱手失之。这就是杜牧做这首诗的本意所在。